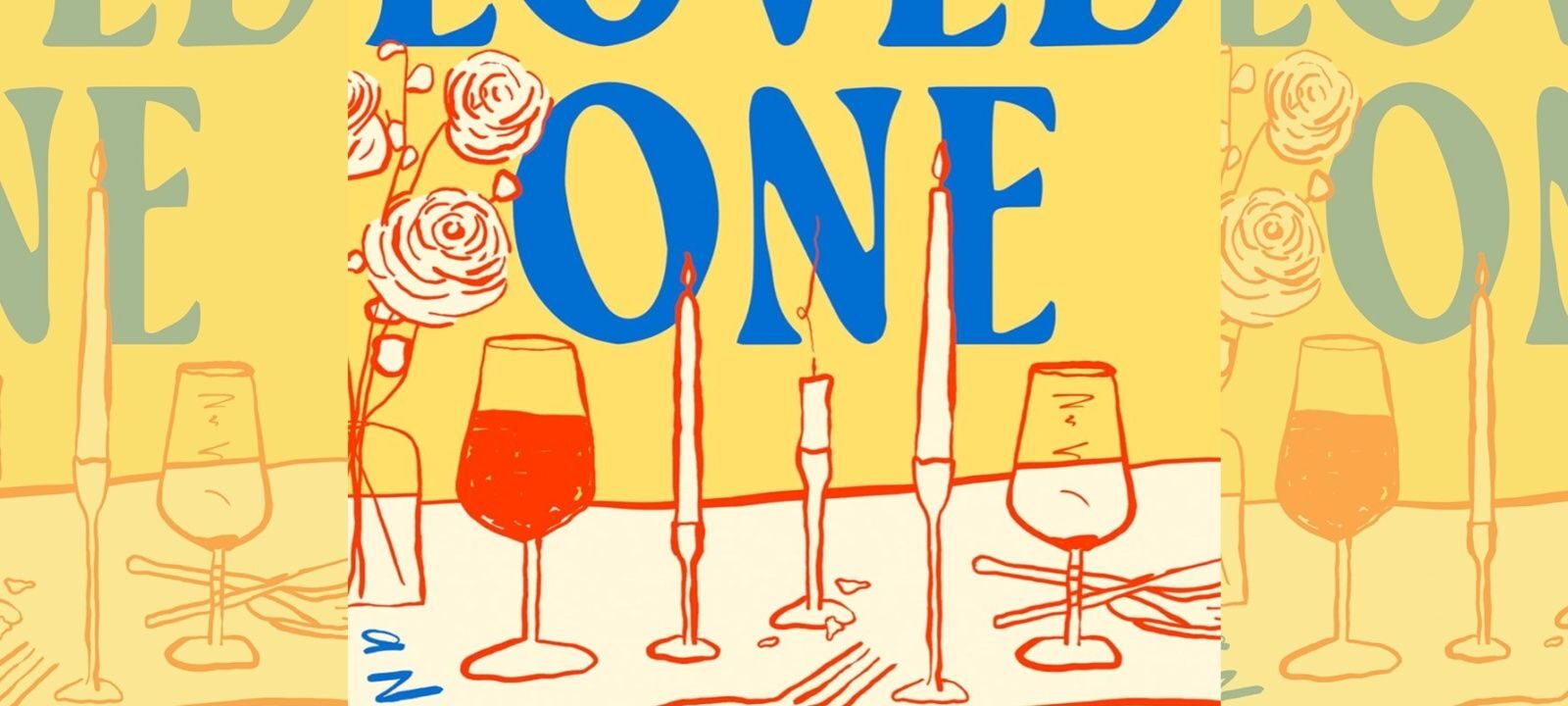关于悲伤的非虚构作品并不少见,从伊丽莎白·库伯勒-罗斯的经典著作《论悲伤与哀悼》,到琼·狄迪恩的《奇想之年》与《蓝夜》。但将这种极度私人又普遍存在的丧失之痛转化为小说,绝非易事。
这正是电视编剧艾莎·穆哈拉尔在其新作《挚爱》中完成的壮举。故事围绕洛杉矶珠宝设计师茱莉亚展开,她正深陷挚友加布(同时也是她长期爱慕的复杂对象)离世的痛苦。在哀伤中,她与加布最后一任前女友伊丽莎白建立了意想不到的情感联结。尽管题材沉重,但穆哈拉尔在《公园与游憩》《善地》《绝望写手》等剧集中磨砺出的犀利喜剧笔触,让阅读过程充满愉悦。
本周,《Vogue》与穆哈拉尔畅谈了《挚爱》的创作历程:如何构建亡者身后的三角关系,深入珠宝设计调研,以及平衡小说与编剧工作。
《Vogue》:新书问世感受如何?
艾莎·穆哈拉尔:百感交集。小说创作是孤独的旅程,所以看到亲友的支持格外感动。有朋友主动协办活动——其中一位开了酒吧,我们与公益组织"芙蕾雅计划"合作。纽约州金斯顿的某家葡萄酒吧启发了书中伊丽莎安的餐厅,当我向女侍者提及此事,得知其丈夫在本地书店工作——现在我们正筹备联合活动。
说实话,最让我兴奋的是与人联结。有位密友专程驱车来金斯顿相聚,当年《公园与游憩》的剧迷和《吉尔莫女孩》播客听众也纷纷现身。我热爱写作的每个环节,但最美好的是思想碰撞——将作品呈现于世,聆听读者的诠释。能与优秀的对话者交流,令我无比期待。
《Vogue》:茱莉亚、加布和伊丽莎白的故事如何诞生?
艾莎·穆哈拉尔:多年前纽约派对后,有位朋友在出租车里告诉我,她的闺蜜正与我的前男友交往。那是位好恋人,我们和平分手,她正是基于我的推荐牵线。但如今他却对那位姑娘很糟糕。我开玩笑说"我又不是男友点评网!"但这让我思考:"那是我的经历,但人会变。或许他们的相处模式不同。"我好奇:"如果我们相遇,视角会重合吗?"
这个念头萦绕不去。《公园与游憩》结束后,我决定实现大学以来的小说梦。虽然电视事业很成功,但写长篇始终是童年夙愿(高中时还出过非虚构作品)。当时剧集完结、尚未生育、新婚燕尔,我想"此时不写更待何时?"出租车对话便成了灵感来源。
当时我正因个人经历思索失去。有位失去祖父的朋友——她知道我经历过多次亲密之人离世——称我为"悲伤专家"。这称号不算动听,却让我意识到值得探索的领域。虽然如今悲伤主题书籍众多,但当我动笔时,纯文学中这类作品很少。回忆录居多,而我想写些不会加重读者痛苦,甚至能带来慰藉的文字。
"失去"与"爱"两个主题在脑海中交织,最终化为茱莉亚与加布的故事。伊丽莎白加入后,情节超越了简单爱情,变得更为复杂。我想探索女性之间的三角关系——这种鲜少被呈现的视角,并为熟悉的情感模式增添层次。
《Vogue》:珠宝描写极具质感,为何选择这个职业?
艾莎·穆哈拉尔:我做了大量调研,采访珠宝设计师并研读工艺资料。茱莉亚有艺术天赋却不像加布投身音乐那般决绝,她的财务背景促使她选择务实又富创意的领域。珠宝设计恰如其分——兼具艺术性与手工质感,甚至带着粗粝感。她要焊接金属,会烫伤手指,不仅是光鲜设计,还要经营小本生意、追讨账款,游走时尚圈边缘却格格不入。
《Vogue》:如何平衡写作与编剧工作?
艾莎·穆哈拉尔:相当艰难!写《善地》第一季时,我早十点到晚五点写作,晚六点熬到凌晨一点。后来在剧集间歇期(《善地》二、三季与《绝望写手》之间)专注书稿。曾幻想在古堡或作家公社浪漫创作,现实却是深夜独自码字。到拍《绝望写手》时,我已找到经纪人,正在进行书籍编校与推介。过程毫不光鲜,但终究完成了。
书稿虽基本完成,仍需修改语句、处理出版细节、增删内容。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。
本次访谈经过编辑与精简。
《挚爱》
售价28美元
书店有售